类别:行业资讯 发布时间:2023-07-03 16:34:23 浏览: 次
KK体育本文通过梳理赵树理小说《“锻炼锻炼”》的批评史,向我们展现了三种不同的现实类型:客观性现实、概念式现实与浪漫化现实。文章具体分析了对此小说的各种批评,涉及到文艺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反映现实以及应当反映怎样的现实等问题,进而指出,从1959年到1961年,赵树理的“事实”进一步被事实化,或者说,他的“现实”进一步被客观化。正是在这里,在经历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之于“修正主义”的两次批判之后,赵树理倒是与“修正主义者”意外地同时也必然地重逢了:“反映客观现实”。
原文发表于《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6期,并入围“第八届(2018年)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感谢朱康老师授权保马推送此文!
1957年12月,《人民文学》杂志社改组,由张天翼任主编(1957年12月-1966年5月)的编辑委员会替代了原本由严文井挂名任主编(1955年12月-1957年11月)、秦兆阳任副主编但实际负责(1955年12月-1957年4月)的编辑委员会,赵树理第二次成为编辑委员会委员(1957年12月-1966年5月,第一次在1953年1月至8月间)。这次改组不仅是一次人事的变动,还是一次思想的批判,它体现了对秦兆阳办刊方针的全面清算。到了1958年9月,《人民文学》在头条位置重点推出了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刘白羽(正是他在1955年12月动员秦兆阳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在7月举行的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秦兆阳的破产》,并在紧随其后的版面上,转载了原刊登在《火花》1958年8月号的小说《“锻炼锻炼”》。这两篇原本来自不同语境、不同文类的文字,因此构成了一种连续性的上下文,而在该期《编者的话》中,《人民文学》又在它们之间建立了一种互文性的关系。《人民文学》的编者沿着刘白羽的“概括性的、透彻的剖析”,判定秦兆阳是“反社会主义‘英雄’”,他任副主编时把《人民文学》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在上面“插上修正主义的白旗”,并种下了《改选》(李国文)、《本报内部消息》()等“几株毒气特盛的毒草”,而与之对照,《“锻炼锻炼”》则是“深入生活的作家”所“努力创作”的“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伟大作品”,是“近年来小说创作方面可喜的收获”,代表着“白旗”拔除之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红旗”之下培植出的“社会主义文艺花朵”。[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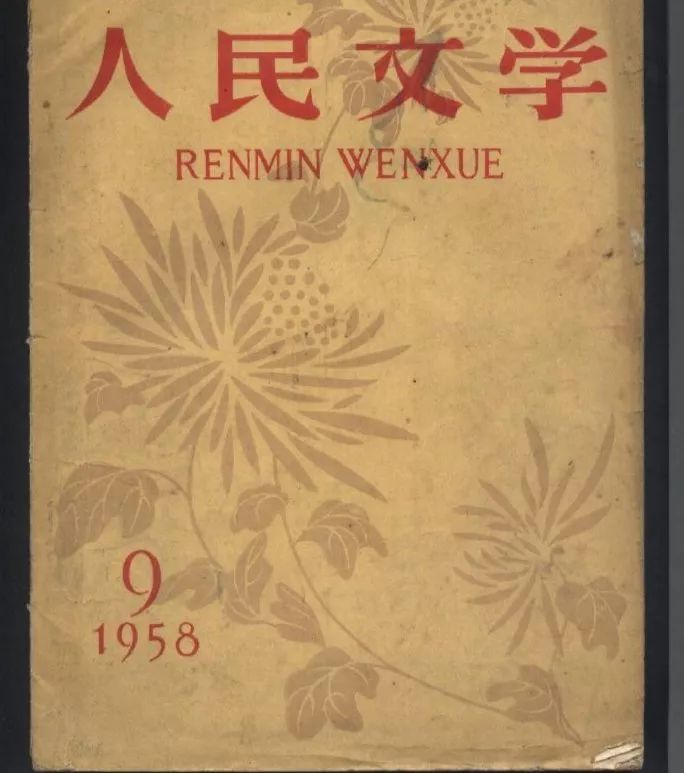
“(插)红旗”与“(拔)白旗”是在1958年5月5-23日举行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所多次使用的隐喻,在那里,在批判了教条主义者“照抄外国”与修正主义者“从资产阶级老师那里搬点东西”之后,紧接着就号召“要敢于插红旗”,因为“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而“资产阶级插的旗帜,我们要拔掉它”。“修正主义的白旗”,就是在这样的语境里所形成的表达,而在上述《人民文学》的《编者的话》的话里,它主要指的是秦兆阳以何直的笔名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中所提出的“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在那里,秦兆阳“想以文学的现实主义为中心,来谈一谈教条主义对我们的束缚”,为此,他为一切文学的现实主义设定了一个基本的大前提:
文学的现实主义……是指人们在文学艺术实践中对于客观现实和对于艺术本身的根本的态度和方法。这所谓根本的态度和方法,不是指人们的世界观……而是指……以无限广阔的客观现实为对象,为依据,为源泉……追求生活的线]
从这样的前提出发,秦兆阳看到,起始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其定义中包含着“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与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的要求,但由于“社会主义精神”属于“人们的世界观”,是抽象的观念,这一要求会导致“让血肉生动的客观真实去服从这种抽象的固定的主观上的东西”,从而脱离客观现实而塑造出一种概念式的现实。因此秦兆阳提出用“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要求作家自觉到客观现实、忠实于客观真实并充分地表现客观真实,不是让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从外部与艺术描写教条地结合,而是让它在艺术思维里发挥血肉生动的作用,从而探索出一条充分发挥创造性的、现实主义的道路。
正是秦兆阳以“教条主义对我们的束缚”为目标的批判,使刘白羽能够在1958年7月上溯到发表于《人民日报》1957年6月19日的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那里寻找批判秦兆阳的“文学的现实主义”的政治基础与理论基础。根据在这一讲话中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区分,刘白羽将秦兆阳与“我们”之间的分歧确认为“敌我矛盾”;根据在这一讲话中对“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描述,刘白羽将秦兆阳指证明为“现代修正主义者”。刘白羽引用了这一判断:“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他没有引用但却以之为自己批判思路的是其后的两句:
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4]
由此,秦兆阳基于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评,就成为现代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而他在两种现实——客观性现实与概念式现实之间所作的区分,就成为现代修正者“施展诡辩术割裂马列主义词句”的例证。在刘白羽看来,苏联文学家高尔基早就区分过两种现实,而秦兆阳站在与高尔基完全对立的立场,完全颠倒了高尔基的“词句”之所指。高尔基说他看见了“两个真实”:

其中一个真实——是你们的、陈旧的、衰老的、瞎了左眼的——没有牙齿,吃着它自己制造出来的腐烂东西。另一个——是年青的,血气旺盛的,充满着无尽多的精力的,它热望向着自己的崇高目标前进,毫不回顾。[5]
对刘白羽来说,这前一个“真实”是秦兆阳以“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之名念兹在兹的“客观现实”,一种由“盲目自发论”所主导的现实;这后一个“真实”是秦兆阳所批判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现实,一种在“社会主义精神”之下向着前进的现实。刘白羽要从秦兆阳的批判中恢复与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于是,在秦兆阳那里作为“抽象的概念式的东西”来理解与批判的“社会主义精神”,在刘白羽这里是一种能够“教育人”进而通过人民来体现创造性与未来指向的力量,在这一力量之下,现实也就不再是客观的对象,而是“精神”、“概念”之于“客观”的否定与综合的进程,是被“精神”、“概念”介入了的现实,或者说是这一意义上的概念式的现实。在刘白羽看来,“不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就用资本主义精神教育人,二者必居其一”,因此,秦兆阳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表达的其实是一套“从精神上瓦解社会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公式”。
[6]在这里,如果仅以“现实”的概念为焦点,刘白羽显然将秦兆阳的两个“现实”做了一个颠倒:概念式的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而客观性的现实不过是对现实的歪曲。正是沿着这同样一个思路,严文井在同期杂志上批判经秦兆阳之手发表并受到秦兆阳肯定的《本报内部消息》时,称之为“用歪曲现实生活的手法”写出的宣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张的反动作品”。[7]
赵树理从未在其文中谈论过秦兆阳,不过,当《“锻炼锻炼”》在这样一种上下文里被转载,他也就被放在了秦兆阳的“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的对立面,放在了以概念式现实为对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边。所以在《人民文学》1958年12月号上,龙国炳从“《人民文学》今年刊载的几十篇短篇小说”中选择了《“锻炼锻炼”》、《典型报告》(李德复)等16篇作品作为“短篇小说的收获”,认为它们“不但及时反映了现实生活,而且走在现实的前面”;
[8]在这16篇作品中,《“锻炼锻炼”》、《新结识的伙伴》(王汶石)等6篇被选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学小丛书”,对此,在《文艺报》1959年第1期(1月11日出版)上,巴人接续龙国炳的“收获”说而“略谈短篇小说六篇”,宣称它们“不仅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且是先行于现实生活的”,写出了“人民‘所愿望的’和现实发展中‘所可能的’”。[9]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巴人。他当时的身份之一是《文艺报》的编委,一个月之后,他在《文学评论》1959年第1期(2月25日出版)上发表了他原本应《文艺报》约稿在1958年1月间写成的《现实主义,还是反现实主义——对冯雪峰“现实主义”理论的初步批判》,在该文中,他将冯雪峰的“现实主义”理论定性为“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为此,他的批判从冯雪峰的“现实主义‘反映论’”开始:
第一,为了反对“公式、主观主义”或“教条主义”,他强调“感情生活”决定一切。第二,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他强调“人的思想只要反映客观现实,就是真理”。第三,……作家必须以内心力或理想力肉搏现实,这样才能产生艺术力,而有艺术作品。[10]
[11]从这样的“反映论”向前推进,巴人为冯雪峰的“现实主义”归纳了四点中心内容:以创作实践代替生活与革命实践,使艺术代替政治,通过反对“写政策”来反对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用对现实的“客观反映”来代替社会主义艺术的党性。而在冯雪峰“反对‘写政策’”的地方,巴人举了赵树理小说来作为反对这一“反对”的例证:
不论是《李有才板话》和《三里湾》,……都没有不贯彻党的政策精神的。在党的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号召下而产生的成功的作品,就证明了冯雪峰理论的反党性质。[12]
这是全文中唯一一处涉及赵树理的地方——但也只写到他的小说而没有提及他的名字,但却包含着巴人对赵树理的全部肯定的态度,他由此要肯定的是,在冯雪峰“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地方,赵树理的小说所体现的是对这一“否定”之否定。于是5个月之后,他写作了《略论赵树理同志的创作》,发表在《文艺报》1958年第11期(6月11日出版)上由《文艺报》副主编陈笑雨组稿的“山西文艺特辑”。在该文中,巴人选择《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与《三里湾》作为代表作来考察它们所反映的生活面貌和所表现的主题思想的发展,尤其是重点讨论了《三里湾》(1955),从中他看到:
在作者的笔下,出现了新的萌芽,新的力量,这就是作者已经用社会主义的精神面貌来丰富他所创造的新的一代人物了。而这,我以为正是作者今后所要努力的方向。[13]
也就是在我国中业已涌现的和在将要到来的技术革命高潮中,会大量涌现的征服世界、征服自然,具有理想的英雄人物的创造。那时候,我们作家的现实主义的笔调,怕也将加添了生气横溢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了吧。[14]

[15]《文艺报》在1958年第9期(5月11日出版)根据的说法组织诗人所笔谈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简称“两结合”。从这样一种期待出发,当赵树理两个月之后在《火花》发表《“锻炼锻炼”》,巴人的感受或许非常的复杂,因为那里没有“”,当然也没有“业已涌现的”“技术革命高潮”,更没有“具有理想的英雄人物的创造”,但它又的确是《三里湾》的延续,因此,他在《略谈短篇小说六篇》中写道:
这作品对我们建设农村社会主义生活是有积极意义的。虽然作者所塑造的先进人物杨小四和高秀兰,还只停留于[《三里湾》的]“王满喜”和“范灵芝”一类人物同样的精神状态里,没有给以应有的提高,提高到有更远大的理想境界,这是一个缺憾;但这也许由于作者所构造的情节太过戏剧性了,因而主题思想的发挥受到情节的限制——情节也可以转过来局限主题思想的发挥的。[16]
在这里,《“锻炼锻炼”》有《三里湾》中某些“先进人物”的——亦即社会主义的——“精神状态”,但没有“更远大的”——亦即的——“理想境界”。这意味着,它有“现实主义的笔调”,但没有“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或者说,它只停留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没有提高到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这也正是龙国炳所说的:“如何在小说创作中,更好地运用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还是很值得我们去深刻探讨的一个问题。”不过,巴人虽然将此看作赵树理写作的“一个缺憾”,但他把原因归在“情节的限制”,由此就削减甚或免除了赵树理的思想或观念的责任。这是一种辩护性的甚至是保护性的批评,可以认为,这是巴人在其可能的范围内以最低程度的否定来换取并维持对《“锻炼锻炼”》的最大程度的肯定。
《“锻炼锻炼”》、“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与“反映人民内部矛盾”
就在龙国炳发表《短篇小说的收获》的次月,巴人发表《略谈短篇小说六篇》的前夕,时任文化部长、作协主席的茅盾写作了《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短篇小说的丰收”),随后发表在《人民文学》1959年的第2期。正如“丰收”不仅是“收获”,还是丰盈的“收获”,茅盾同龙国炳一样讨论“过去一年来的短篇小说”,只是其依托的媒介为1958年的全国范围的刊物而不止于1958年的《人民文学》。茅盾为自身的讨论设置了五个分标题,其中,第一、二个分标题旨在描述性地呈现“丰收”:“一鸣惊人的小小说”、“丰富多彩的劳动人民英雄形象”;第三至五个分标题则重在理论性地分析“问题”:“关于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提高工作中的两个问题”。龙国炳与巴人评述的作品有一部分就被茅盾系属在这里的第二至四个分标题,例如,《普通劳动者》(王愿坚)、《新结识的伙伴》(王汶石)涉及“丰富多彩的劳动人民英雄形象”,《小技术员战胜神仙手》(范乃仲)关乎“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一个温暖的雪夜》(刘白羽)则属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龙国炳与巴人的评述中完全不见“反映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术语,而茅盾的讨论中完全不见《“锻炼锻炼”》这一作品,但龙国炳与巴人却又是在这一作品的周围保持着通向这一术语的可能。龙国炳说自己在阅读中——
看见了人民内部先进和落后、保守和反保守之间的思想斗争(“锻炼锻炼”、“小技术员战胜神仙手”)。就是在整风、大辩论胜利的基础上,人民群众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17]
《锻炼锻炼》的作者……让以杨小四和高秀兰为代表的先进力量暂时当了权,同那以“小腿疼”与“吃不饱”为代表的落后力量,展开了一场戏剧性的斗争……[他]是为我国农村生活中两条道路——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斗争这个巨大的主题思想所推动的。[18]
过去一年内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短篇小说大抵属于上述两类:进步与落后、保守的矛盾,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的矛盾。[19]
龙国炳与巴人从《“锻炼锻炼”》中所离析出的两种“斗争”,正是茅盾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总名之下所区分出的两类“矛盾”,而龙国炳为“先进和落后”的“斗争”所举出的两个代表性作品——《“锻炼锻炼”》和《小技术员大胜神仙手》,只有后者被茅盾选作了“关于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例证。在龙国炳与巴人的表述中,《“锻炼锻炼”》其实就是一部“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短篇小说”,它只是在“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上包含着“缺憾”,但茅盾用其沉默暗示,《“锻炼锻炼”》不仅未能实现“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而且还在“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向上存在着问题。

或许,可能,在茅盾看来,《“锻炼锻炼”》在1958年本就具有另类的性质。1958年8月,当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在《火花》杂志登载之际,茅盾在《处女地》月刊发表了他6月10日在作协沈阳分会座谈会上的发言《关于革命浪漫主义》,正在要求作家“革命浪漫主义地反映这个革命浪漫主义时代”,要求作家“以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来反映我们这时代的天天出现到处出现的奇迹——社会主义时代的生活面貌以及创造这些奇迹的人物的精神面貌”。“社会主义时代”就是“这个革命浪漫主义时代”,因为——如他在《短篇小说的丰收》中所说——“我们的现实生活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我们社会现实的本质是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结合体”。
[20]之所以文学必须运用“两结合”的方法,是因为现实已经具有“两结合”的本质。在这里,随着时代的到来,“现实”的概念发生了转变,它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要求的概念式现实,转变成了“两结合”所对应的浪漫化现实。不过,现实本身的浪漫主义属性并不会使得对它的现实主义反映自动获得浪漫主义特质,茅盾看到,在1958年——
……在前一例中,作者有革命浪漫主义但缺乏革命现实主义,在后一例中,则正相反。[21]
正如“我们这时代天天出现到处出现的奇迹”是人们在生产中“创造”的结果,在文学中唯有通过“结合”才能实现“结合”,唯有在文学中实现了“两结合”才能去反映现实的“两结合”。但这并不意味着,缺乏革命革命现实主义的革命浪漫主义与缺乏革命浪漫主义的革命现实主义并不是对等存在的关系,“革命浪漫主义时代”这一说法表明了革命浪漫主义的优势地位,因此,在这个时代,习得革命浪漫主义是容易的,困难的倒是革命现实主义。在1959年2月18日中国作协召开的文学创作工作座谈会上,茅盾作《创作问题漫谈》的发言,接续《短篇小说的丰收》而继续分析1958年的作品,他指出:
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固然很充分,革命现实主义,也就是对现实的科学分析,还嫌不足,……就大部分作品而言,总还觉得欠缺细致的科学分析。[22]
对现实科学的分析不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个人觉得,从作品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不够深入可以看出来。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作品本来不多,而内容深刻的尤其少,……[23]
对现实的科学分析表现在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深入反映,因而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就成了“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或者说,人民内部矛盾有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反映方式。从《关于革命浪漫主义》到《创作问题漫谈》,虽然茅盾从来没有提及赵树理的名字,但他的论述却潜在地构成了对《“锻炼锻炼”》的批评,特别是当他说“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作品本来不多,内容深刻的尤其少”的时候,这否定了龙国炳与巴人对《“锻炼锻炼”》的思想内容的肯定,由此无异于确认:《“锻炼锻炼”》执行的是一种缺乏革命浪漫主义的革命现实主义,一种欠缺细致的科学分析的革命现实主义,一种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不够深入的革命现实主义。
赵树理同志的短篇小说《锻炼锻炼》在去年8月号的《火花》发表后,去年9月号的《人民文学》曾予以转载。这篇小说在读者中激起了很不相同的反应:有些热烈地欢迎这部短篇小说,认为小说线年整风运动中农村生活的一个片段……有些读者却认为这篇小说歪曲了现实生活。我们认为对这篇小说的估价和分析,涉及到文艺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如何描写生活中的落后现象、如何运用讽刺等问题。这些是目前文艺创作中、文艺作品的阅读和欣赏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企图通过《锻炼锻炼》以及其他类似作品的讨论,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24]
一篇1958年8月发表的关于“1957年整风运动”的小说,由于读者对它的反应分裂为“真实地反映”与“歪曲了现实生活”这两个评价的方向,所以从1959年4月开始,被纳入一个关于“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持续的讨论。在这里,无论是时间,还是主题,《文艺报》的《编者按》都呈现出某种断裂和迂回,它沿用了茅盾在“现实”与“人民内部矛盾”之间所设置的内在关联,但不同的是,它既没有像《短篇小说的收获》那样把“两结合”与“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并列为两个同等的主题,也没有像《创作问题漫谈》那样将“反映人民矛盾”看作是“对现实科学的分析”的佐证,相反,它把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或“歪曲”的“反映”,回收到了“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中。事实上,这份《编者按》对读者的两种“反应”的描述,就是对该期“文艺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专栏内三篇文章内容的概括:张庆和《读小说〈锻炼锻炼〉》与姜星耀《喜读〈锻炼锻炼〉》持“真实地反映”的观点,武养的《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题目就是它自身立场的表达。这三篇文章没有任何一处谈及“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话题,甚至没有任何一处出现“矛盾”这一词语。尤其是武养的文章,在三者之中它最具论文的规模与气质,而它唯一关心的是《“锻炼锻炼”》与“现实”的关系,或者说关心的是《“锻炼锻炼”》在现实主义理论光谱中的位置。事实上,它标题中的“歪曲现实”一词就是前引严文井批判《本报内部消息》的用语,而只需沿着严文井的批判路径再向前推进一步,就可以将《“锻炼锻炼”》判定为宣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张的作品”,就像后来王西彦所说的那样,“按照武养同志的逻辑和情绪看来,赵树理同志这次是给了读者一株毒草”。
武养的文章引起高度的关注与巨大的争议,以致《文艺报》在1959年第9期上第二次以专栏形式讨论“文艺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时,所组织的8篇文章有5篇都是对于武养的反批评。因而是否“歪曲现实”仍是该期专栏讨论的第一主题,而直接提及“人民内部矛盾”一词的只有3篇,直接讨论“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只有汪道伦《歪曲了现实吗》一篇:
作品能否反映社会的真实首先取决于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能力和写作态度。人民内部矛盾是错综复杂的。作家要正确的反映这个矛盾,必须首先认识这个矛盾,否则就不能写出矛盾发展的真实性,也即我们社会发展的线]在这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被汪道伦放在了“(反映)社会的真实”与“(写出)社会发展的真实性”之间,它仍只是一个从属于“反映现实”主题的次生主题。事实上,直到《文艺报》1959年第10期,它的专栏讨论才完全回到了它的专栏主题,该期专栏的唯一一篇文章——王西彦的《〈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算是该专栏三期讨论的结论。王西彦紧扣“如何反映”这一核心字眼,一方面在一般意义上阐明“怎样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我们所采取的立场”;另一方面则以《“锻炼锻炼”》为范例,不仅从写作立场上高度肯定了赵树理“把生活里面的消极现象,确定写成消极现象,而且是前进中的新社会里面的消极现象”,由此肯定赵树理刻画了农村中的落后分子及他们的组织根源,展现了“两条路线的矛盾斗争——整风和采用鼓励资本主义思想的‘老经验’的矛盾斗争”,
[26]正是从这样一种对《“锻炼锻炼”》的认识出发,王西彦将武养的批评看作一种“轻率而粗暴”的“戴帽子,挥棍子”的行为。他要求通过对具体作品展开讨论,弄清楚文学上的重要问题,为此他把自己对武养的反批评提升到战斗的高度:
武养通过将《“锻炼锻炼”》看作“歪曲现实的小说”,把赵树理置入一个“敌我矛盾”的结构;王西彦则通过确认《“锻炼锻炼”》是“一篇很好地反映了人民内部矛盾的作品”,把赵树理唤回到“人民内部”。而将武养的评论与刘白羽对秦兆阳的批判、巴人对冯雪峰的批判联系起来,可以看到某种具有悖论意味的理论场景:对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根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而对“反映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包含着政治概念的命题的讨论,倒首先是一个文学问题。

正是在这里,有必要简单回溯“人民内部矛盾”、“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与“两结合”之间交错的历史。“人民内部矛盾”,原本是由主持起草、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于1956年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的概念,在那里,它指的是国际方面相对于“敌我矛盾”这一根本矛盾而存在的一种非根本矛盾。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在国内方面区分了“敌对阶级之间”与“人民内部之间”两类矛盾,并继《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之后再次论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该讲话传达后,在党内,尤其是在各级党报并未引起积极的反应,《人民日报》没有就此发表社论,倒是把“人民内部矛盾”呈现成了一个仿佛是文学的问题:3月19日,它发表了欧阳予倩《听了毛主席报告的几点体会》与张天翼《文艺怎样表现人民内部矛盾》。从1957年4月10日开始,《人民日报》在的干预下连续发社论阐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 1957年5月1日,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更是指出:

[28]经多次修改以后,的讲话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于1957年6月17日的《人民日报》,自此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人民内部矛盾”一直主要作为政治问题与哲学问题被广泛地讨论。而在文学界,自1957年3月蔡仪在《文艺研究》发表《论现实主义》、4月蒋孔阳在《文艺月报》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来,直至1958年2月周扬在《人民日报》发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各种意见争锋的焦点,又是一切讨论最后的结论。在1958年3月提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1958年5月《文艺报》组织“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笔谈后,周扬于1958年6月《红旗》创刊号上将“两结合”的诗歌命题扩大到整个文学领域,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宣布:
所谓“当前时代”即“”的时代,如《人民日报》在1958年2月2日社论中所宣布的,“我们国家正面临一个全国的新形势”。
“两结合”是根据正在发展中的“”的“特点和需要”所提出的主张,也因此,在1958年,它是文学界最为关切的理论命题,同时也是最难掌握的创作方法。而当“”正处在发展的高潮之中,中央于1958年11月21-27日武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要压缩空气”,“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31]批评与纠正“”中的“左”倾“冒进”的政策。随之,“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也被局部地修正,“(正确地)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便作为政治纠“左”的文学表达或文学纠“左”的政治论述,作为对革命浪漫主义的限制、对革命现实主义的补充而成为1959年讨论的重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赵树理的《“锻炼锻炼”》才会在发表了8个月之后忽然变成焦点:它以“一九五七年秋末……整风时候”[32]为背景的小说更容易通过整风运动的主题设定来抵达“人民内部矛盾”。事实上,当茅盾批评“作品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不够深入”的《创作问题漫谈》发表时,赵树理正在山西省文联理论研究室谈论“创作问题”;在《文艺报》关于“文艺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讨论结束之后,《火花》在其1959年6月号刊登了赵树理的谈话记录稿《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赵树理所谈论的“问题”包括四个方面:关于表现新英雄人物问题;如何表现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关于写作技巧问题。这些“问题”与茅盾在《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中的“问题”有三个大致重合,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个问题上,他没有沿用更普遍的“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说法而采纳了张天翼的“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的措辞。而关于“如何表现”,他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抓主要矛盾”:
[34]以这两个意见为前提,赵树理从自己的小说中选择了《李有才板话》《三里湾》《“锻炼锻炼”》这三部作为“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的例证,展开了一个文学上的自我批评的工作。在这三部小说中,赵树理最后的落脚点在《“锻炼锻炼”》,他不仅讨论了其中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状况,还呈现了其中的具体人物,将他们普遍化为一种类型:
《“锻炼锻炼”》这篇小说……我想批评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中农当了领导干部,不解决他们这种是非不明的思想问题,就会对有落后思想的人进行庇护,对新生力量进行压制。……这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王聚海式的、小腿疼式的人,狠狠整他们一顿,犯不着,他们没有犯了什么法。可是他们思想、观点不明确,又无是非,确实影响了工作进展。对于他们这一类型的人,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把事实摆出来,让他们看看,使他们的思想提高一步。现在各地虽然都已经公社化了,但这类思想还是存在着的,我认为写写还有用处。
[35]与龙国炳、巴人、王西彦等评论家把小说里的人民内部矛盾类型化为思想矛盾与路线矛盾不同,赵树理把他所展现的人民内部矛盾具体化为有特定思想的人的矛盾,由此弱化矛盾的尖锐程度,抑制矛盾的隐含倾向,防止它们有任何转化或升级为敌我矛盾的可能。这一矛盾涉及到三个方面——中农干部(农业社主任王聚海)、有落后思想的人(两个女社员“小腿疼”与“吃不饱”)与新生力量(即前文中巴人所说的“以杨小四和高秀兰为代表的先进力量”,农业社里的两位青年副主任),作者站在新生力量的一边,把中农干部与新生力量之间的矛盾确认为主要矛盾,而落后思想的人与新生力量的矛盾自然就处于次要矛盾。但在这里,他并没有根据其自己设定的前提去讨论主要矛盾的解决,更是没有提及解决矛盾的主要动力——党,虽然《“锻炼锻炼”》本来写了支部书记;而在小说原文之中,他也的确只解决了次要矛盾,让作为新胜利力量的杨小四、高秀兰与有落后思想的人“小腿疼”面对面斗争,迫使她暴露与检讨自己思想的落后,但对于主要矛盾,对于身处主要矛盾中的这位中农干部,小说给了一个开放的结尾,在那里,在杨小四带领社员与“小腿疼”、“吃不饱”的落后思想作斗争的会议结束以后——
[36]社主任王聚海作为有“是非不明的思想问题”的“中农干部”需要“锻炼锻炼”,但如何“锻炼”,赵树理并没有在小说内部提供路径,而是在小说外部,通过让他以读者的身份“看看”“摆出来”的“事实”从而使“思想提高一步”。向何处“提高”呢?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到,赵树理把中农干部的思想问题界定为“是非不明”,是在有意地呼应或征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理论界定:
[37]所谓“锻炼锻炼”,亦即从“是非不明”提高到“分清是非”。于是原本发生在新生力量与中农干部之间所要分清的是非问题,变成了中农干部自身在认识上所要分清的是非问题:人民内部矛盾转化成人民“内部”矛盾,或者说,人民内部矛盾本来就同时是人民“内部”矛盾。
恰值《文艺报》关于“文艺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讨论落幕的时刻,作协武汉分会举行了关于“文学创作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座谈会。正如其名名称所示的那样,这次座谈会是对《文艺报》的讨论的自觉的延续,会上不仅多次批判了武养的观点,还多次分析了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而就在《火花》发表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的当月,作协武汉分会的机关刊物《长江文艺》刊登了于黑丁(时任该分会主席、《长江文艺》主编)、胡青坡(时任该分会副主席)KK体育、赵寻等人在座谈会上的发言,由此而至9月,它用一个与座谈会同名的专栏推出了一组相关的讨论。这组讨论的基本立场其实就是《文艺报》的基本结论,在华中师范学院当时编的《文艺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中,于黑丁、胡青坡、赵寻三人的发言与王西彦的《〈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一同被列为“参考文件”。然而,与《文艺报》的讨论相比,这事实上是一组虽得其题,未逢其时的讨论。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与八届八种全会——史称“庐山会议”,众所周知,由于彭德怀的“”,这个会议在上山时意图还在纠“左”——纠正“左”倾的冒进,下山时结论已在“反右”——反对“右倾”的保守——了。“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政治纠“左”的文学表达当然必定会受到冲击,于是《长江文艺》在1959年11月暂停出刊而在12月出双月合刊,并自此开始推出了一个“文学作品如何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的专栏,专栏的《编者按》宣布要“以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精神作为武器”再行讨论“文学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KK体育。
“如何反映”被替换为“如何表现”,由此在《长江文艺》的内外开启了一系列批判。这一系列批判的顶点在1960年2月,湖北省委书记许道琦在《七一》发表了《对于‘文学创作如何反映人民矛盾’的讨论的批判》,《文艺报》第4期随即转载并将标题改为“驳于黑丁等关于文学创作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谬论”,同时以“本报记者”的名义配发了专题报道《关于文学创作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辩论》,宣称“于黑丁和胡青坡……重复了修正主义者的观点……掩饰了人民内部矛盾中的阶级斗争”。[39]阶级斗争是一种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中的阶级斗争”这一措辞将原本性质不同的两类矛盾放进同一个矛盾的结构,通过在“人民内部”再分“敌我”,它中断了“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路径,因为人民的概念已被置入一个不断激进化与纯洁化的过程。04
小在《人民日报》1960年1月1日的社论里,“人民”已被纯化为“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了的、被思想教育了的、思想解放、敢说敢做的人民”,而这样的人民——
[40]“连续跃进”,“继续跃进”,“更好的跃进”……在短暂的纠“左”之后,“跃进”重新来临,作为政治纠“左”的文学表达的“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就只能将其理论意义完全还回“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1960年7月22日至8月13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三次文代会)召开,周扬代表文联作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茅盾代表作协作了《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的报告。周扬的报告经过了审读,并被写进大会的决议,在那里,面对“社会主义建设以空前速度持续跃进”,周扬宣布:
[42]而在专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一节中,周扬只在讨论“革命现实主义”时,在一个段落的一小部分里说到“我们正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的矛盾”,但没有提及“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了一个自我取消的概念;连在其报告中仍在宣讲“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茅盾,他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也已从“进步与落后、保守的矛盾,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的矛盾”走向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一“今天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实际上已是一种受“敌我矛盾”规定的矛盾,“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成了一个空洞的理论位置,它不再是“革命现实主义”的自然延伸或有效成分,因为“现实”已发展为或被限定为周扬所说的“社会主义现实”,一种由“先进的理想”转变而来的“现实”。“社会主义现实”是“两结合”的理论赌注,它在文学中显形与否测绘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周扬的论述中:
修正主义者……企图把社会主义作家拉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他们以“写真实”为借口来反对文学艺术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崇高任务。我国秦兆阳就是这样。……他们……看不见社会主义现实的光辉整体和更光辉的前途。……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起来……正是对于修正主义者的进攻的一个有力回答。
[43]“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对立,转变成了“两结合”与“修正主义”的对立。在刘白羽那里已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否定过的秦兆阳,又经历了一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对他的否定。曾被《人民文学》视为秦兆阳的对立面的《“锻炼锻炼”》,也因此面临着如何在“两结合”的理论里被评价的问题。——但它没有得到这样的评价:周扬报告中的“两结合”一节,主要展开的是理论的论述,没有涉及任何当代的作品;茅盾报告中的“两结合”一节,虽在理论之外引入了当代的实例,但他的几次类似“《创业史》、《百炼成钢》以及马烽、李准、孙峻青、王汶石等等的一些短篇小说”这样的列举,没有提到《“锻炼锻炼”》,也没有涉及赵树理。他们并非是要否定赵树理的意义,在“两结合”一节之外的其他部分,周扬在“对我国人民的革命历史和现实斗争作了广泛的描绘和艺术概括”的“优秀的作品”中列入了《灵泉洞》(1958)与《三里湾》(1955),
茅盾在讨论众多“在作品中体现了民族化和群众化的作家”所创造的“独特的个人风格”时,首先讨论的就是赵树理“明朗隽永而又时有幽默感”的“独特的文学语言”,同时他也肯定了赵树理的具体的小说,他称《三里湾》是“反映农村巨大变革(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脍炙人口的作品”,《老定额》(1959)是“反映人民公社的短篇”中的“优秀之作”。[45]茅盾又一次对《“锻炼锻炼”》保持了沉默,而这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老定额》,按照中央1958年8月29日发布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人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因此,“反映人民公社”同时也就是在反映,就如该小说的主人公——绰号为“老定额”的李家河人民公社“星火大队”大队长林忠所说:“谁也[都]应该!”[46]不过,茅盾并没有因《老定额》对“”的反映而将其归于“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而从赵树理的角度来看,以“人民公社”作为小说“反映”的内容显然是在用背景替代前景:茅盾在论述赵树理的个人风格时曾把“形象鲜明的绰号”认作是赵树理“幽默感”的一种体现,但他却并没有从“老定额”这一绰号去把握赵树理寄寓在其中的批评性的意见。在1966年所写的检讨书《回忆历史 认识自己》中,赵树理写道:

《老定额》的主人公林忠之所以被称作“老定额”,是因为他“把大部分精力消耗在随时修改定额上,因此提意见的人就把他叫做‘老定额’”。而在《“锻炼锻炼”》中,当“争先农业社”的生产停滞,“妇女大半不上地,棉花摘不下来”,支书王镇海要求通过“整风”来“把这种情况变过来”,中农出身的社主任王聚海则提出:
[48]一个“农业社”(高级农业合作社)的故事与一个“人民公社”的故事,在“定额”问题上达成了主题的一致。甚至不仅是主题,还包括小说对“解决主要矛盾的主要动力”的把握。虽然赵树理在1959年6月宣布过“不必篇篇都要写个支部书记”,但发表于1959年10月的这篇《老定额》如同《“锻炼锻炼”》一样有个支部书记的形象,并且也是在结尾,名叫李占奎的支书说:
[49]对于赵树理来说,无论是在主题上,还是在人物关系的设置上,《“锻炼锻炼”》与《老定额》都有足够的理由被归为同一类小说。而正是这种类同性,使茅盾对《“锻炼锻炼”》的第二次沉默显示出一种更深长的意味。在《三里湾》之后,在第三次文代会召开之前,赵树理创作的小说,除了写“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山区人民在日寇和蒋匪军的双重压力下的生死挣扎”的《灵泉洞》,就只有《“锻炼锻炼”》和《老定额》这两个与“农村巨大变革(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相关的短篇。在茅盾的报告里,“反映人民公社”的《老定额》虽然没有进入“两结合”的理论视域,但它至少还是“最近两年中,趁着全国的大流,我们[文学工作者——引者]也有了跃进”的例证,与之相较,反映“农业社整风”的《“锻炼锻炼”》则完全被搁置在了“的大流”之外。对茅盾来说,这意味着,《“锻炼锻炼”》不仅没有用“两结合”的创作原则去反映“革命浪漫主义的生活”,而且它也没有以其自身这样一个文学事实成为“跃进的伟大现实”的一部分,或者说,无论从内部还是从外部来观察,它都远离了现实,远离了“时代”的浪漫化现实。
1960年是“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的年份,因此“两结合”的艺术方法在这一年被正式地确立。当“跃进”在其自身的“继续”中并没有走向“更好”而不得不转入对它自身的政治反思,“两结合”的艺术方法也因此不得不接受对它自身的理论限制。在1961年1月14-18日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国民经济的发展被重新理解为“跃进、调整、再跃进的过程”,由此,在经历了1958-1960年的“跃进”之后,1961年的经济主题确认为“调整”。在全会的最后一天,发表总结讲话,继在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1月13日)上要求“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之后,宣布“六一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调整”、“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它们不仅扭转了经济的政策,同时还改变了“现实”的观念,《人民日报》1961年1月29日的社论重申:“尊重客观事实,依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世界并进而改造世界,这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最起码的态度”。现实重新回到了“客观”的层面,“反映现实”的文学也因此必然发生内容的转换。《文艺报》在1961年第3期(2月11日)发表了由主编张光年执笔的专论《题材问题》,呼吁必须在“歌颂”之外“促进创作题材的多样化的发展”,“反映世界的多样性,反映无限丰富的伟大现实”;
继而,中央宣传部于1961年6月1日至28日召开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讨论由周扬领导起草的《关于当前文艺工作的意见(草案)》并于8月1日印发各地征求意见,该《意见》不仅同样提出了题材的多样化问题,而且对第三次文代会决议的核心要求——“全国文艺工作者必须加强艺术实践,努力掌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51]作了调整:
[52]“必须”变成了“应当”,“掌握……艺术方法”变成了“体现……精神”:“两结合”虽仍居于中心的位置,但被弱化甚或说被移除了主宰、规范与约束的功能;“对他们的要求不能一律”:作家在创作中被赋予了基于个人条件选择的自由,虽然还只是在一定的限度内。
一个一直未与“两结合”相结合的赵树理因此有了自我肯定的空间,于是在这浪漫化现实消退、客观性现实重新上升的时刻,他又一次回到《“锻炼锻炼”》:在《文艺报》关于“文艺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专栏关闭两年之后,赵树理亲自涉入并检视了它所聚拢的对《“锻炼锻炼”》的争论。1961年9月4日,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剧作讲习班上,赵树理宣称“在当前生活中,内部矛盾是主要的”,在这一前提之下,赵树理以自身为例证向学员讲述如何深入与如何写作,其中提及:
[53]原本在1959年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词的争论,在赵树理看来,就是一场关于“现实”的性质的争论:“从概念出发”还是“从事实出发”,亦即,是概念式现实还是客观性现实。在一个“实事求是年”里,赵树理当然站在客观性现实一边,只是对他自己来说,这当然不是一个基于1961年的特殊性质所做出的特殊选择,而是他在写作《“锻炼锻炼”》之际就已经严格坚持的立场,是“合作化到今天”这样一个连续的时段里的连续的“事实”所提出的要求。关于《“锻炼锻炼”》,在1959年6月的《当前创作的几个问题》里,赵树理的态度是“把事实摆出来”,在那里,“事实”是他的对象,而“事实”的中心是“中农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是中农干部王聚海对于“小腿疼”与“吃不饱”这样“有落后思想的人”的庇护;到了1961年9月,赵树理的取向是“从事实出发”,在这里,“事实”是他的前提,而“事实”就是“小腿疼”与“吃不饱”的存在本身。从1959年到1961年,赵树理的“事实”进一步被事实化,或者说,他的“现实”进一步被客观化。正是在这里,在经历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之于“修正主义”的两次批判之后,赵树理倒是与“修正主义者”意外地同时也必然地重逢了:“反映客观现实”。
[3] 何直:《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
理论上的唯物主义立场,政治上的人民立场,推介“与人民同在”的文章,呈现过去和现在的“唯物主义潜流”。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